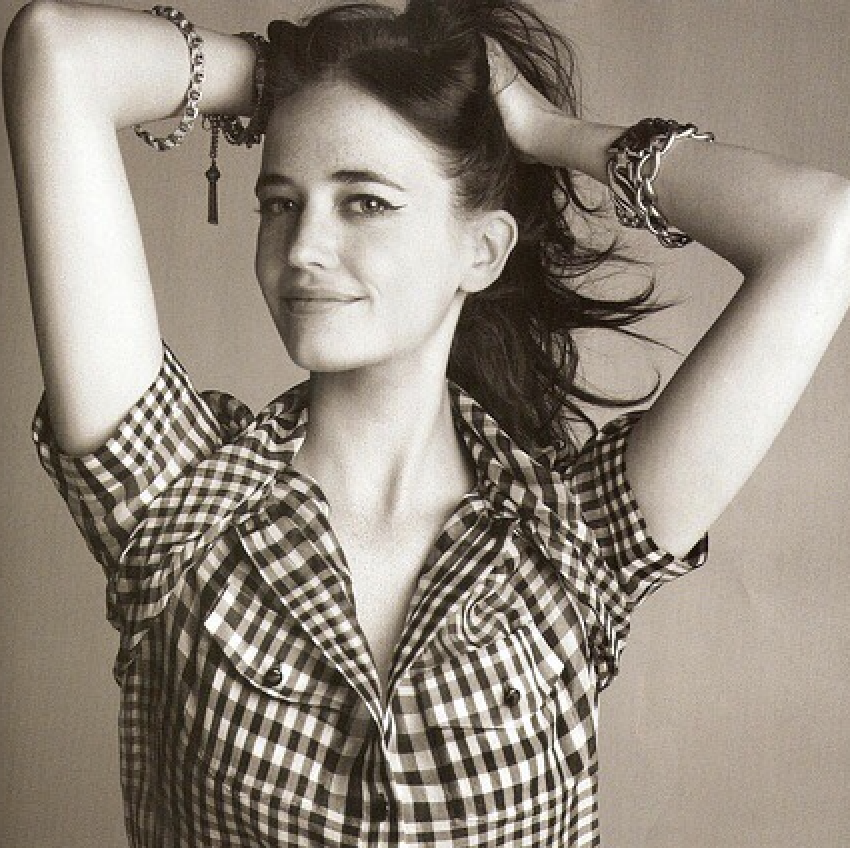我窃自以为,219班绝大多数人对于班主任刘腊辉老师的情绪都有点复杂或是难解的,这与这位老师很不同的教育风格乃至个人性情、人生态度都大有关系。如果前面所说,“殷老师是儒家积极入世的典型代表”这一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刘老师则可以说是道家无为胜于有为的典型。
其实说刘老师这人有多少不同,很多人都不会很同意,因为刘老师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现在我们会想起高中的时光,是否真的有人会觉得刘老师这个人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给自己身上打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呢?应该没有吧。因为他的性情是无为垂拱之治,没有太多豪言壮语,不会八婆的说要你多刻苦多努力,甚至犯了错误也没有苛责的言辞,犯了糊涂也不会和你谈起什么人生哲理苦乐逻辑,这些,都是很难以直接理解的,甚至不可以接受,毕竟高中尤其高三压力太大,毕竟升学确实是人生里意见极其关键的事情,殷老师的激情,彭老师的认真,邹老师的务实,贺老师的努力,Hatty的信心,这些东西无疑更容易让人感觉得到作为大家的领路人的可靠,但刘老师多少打了点折扣,可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一位老师,在我的思考体系里,评价是最高的,一孔之见,纯属抛砖引玉。当然,我们还是先从最小的事谈起,从最老的事谈起。
应该说,我们刚好赶在了刘老师走向比较明显的衰老的时候,大四的寒假,我也终于伸展开涣散的身板,回到一中探望了我的老班主任时,但见刘老师宽颜白鬓,佛陀般的笑脸,家常八卦,还是会有很多不已经的笑话,这一切发生在刘老师身上的美好的东西全都不会变,只是时间在慢慢修饰着它们的颜色,就像七年前老师还是葱茏的黑发慢慢变成慈祥的白,时间也慢慢修饰着它们的棱角,就如六年前老师额头上憨直的线条已经变得平常不奇,时间也慢慢修饰着它们的节奏,五年前老师的步履已经开始放了下来,现在是真的渐渐慢了下来了。前面说人事已过,实在过于轻率,其实人事依旧隐然温存,那一刻的自己,感到浑身各种的舒张,这种随心遂意的张弛之感,与前面任何一位老师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言归正传的说,确实,七年前,也就是高一,印象里的刘老师虽然与殷老师之凌波微步大步流星始终无缘,但与高三时候你轻易就联想到的“蹒跚”二字,那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吧,我还很清晰的记得第一次见到刘老师,白色条纹的衬衣,精神那叫一个畅快,对,是畅快,抖擞这词我打出来了,总觉得还是形容殷老师或是刘忠东老师比较合适。见到我爸和我言辞轻快地问来的真早,几点起来,反正我是少了很多陌生的感觉。课堂上老师笑话很多,这些都能给人以活力、敏捷的感觉。那时候还印象特深刻的事情是,刘成那小样坐在了进门的第一位,每次刘老师一进来,刘成那小一个头就刷地立起来,一口普通话叫到“刘老师”,刘老师半是惊吓半是感到滑稽的说了句,“乔口人就是反应快啊!”,PS. 刘成和刘老师都是乔口人,真是笑疼我了。不过这个小镜头里更加闪光的点貌似是刘成了,嗯,不过其实我是想说刘老师比较随和,喜欢和学生开玩笑,那时候学生们看到刘老师也很乐,像张双、李勇、杨雄等人,也经常和刘老师耍耍嘴皮子,说过些什么不记得了,刘老师这些小习惯三年一直都是有的,不过后面没有那么富有表现力而已,这个原因后面慢慢说吧。
很惭愧的说,我绝非讲故事的能手,我对故事的记忆力很差,这让被工作压榨了太多回忆自由的我此刻真想不起很多素材来好好温习我的班主任,故事于我,完全是蹩脚的侦探遇上了狡猾的罪犯,不过既为侦探,我多少得有自己一套逻辑为自己的这番尴尬狡辩一番,因为刘老师从来都不是一个优秀的出演故事的人。我这一琢磨,能具体回忆起来的就是高二的一个冬天见到刘老师给刘成送来洗好晾干了的衣服,那闲散的样子真让我想起我辞世多年的年年并顺便回忆了爷爷一个下午,然后记起了班上很多人出水痘的时候几乎每节课课余时候都到班上来瞄瞄,想起刘老师有次左脸颊肿得很大,进来教室的一刻,自然引起满堂哄笑,刘老师笑脸憨憨,“这叫面子大!”,算是很逗趣儿的自我解嘲,然后,还有什么呢…对了,又想起一个,有此刘老师右边眼睛不知道怎么了,反正就像很多电影里的海盗一样,遮住了一只眼睛,然后一只手遮住那只眼睛,对大家说,“我这是‘一目了然’”,我觉得这位老师是很重视幽默轻快的,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
另外想起件诡异的事情,高二的时候学校体育艺术节,学校规定是班级的任课老师是可以甚至要求和学生一起参加,刘老师参加是定点投篮的比赛,刘老师那熊样,看上去和我也差不多吧,四体不怎么勤的感觉,居然能做到十发九中,诡异至极。其实大众面前投篮这种多少靠点风水的事儿,心里稍微走神一下,比如虚荣一下,求胜心发作一下,手就要犯贱了,就像樱木花道那“秘密集训射篮”后第一发球,一心以为哥就怎么怎么地了,结果大跌眼镜。刘老师扎实的投篮基础怎么来地,这真是我记忆里一笔糊涂账,或许刘老师也有像刘毅刚、周向阳那样的过去,哈哈,子曰:未可知也。但是我觉得老师确实练就了一番波澜不惊的好心态,你亦不必觉得牵强,如果你耐心看了上文,又愿意耐心看完下文,我觉得这和刘老师整个人的特质是一脉相承的。
再说说刘老师的课堂。就我的认知而言,我觉得一个受到学生欢迎的课堂,最需要的就是一个优秀的表演者。不过说实在的,对于表演,尤其是作为课堂表现力最重要一环的表演力,我举的他本人对这个也没多少兴趣。你去听刘老师的课,都是淡淡的讲解直如旧友闲聊,所以在高一高二的时候这样的课堂应该是受欢迎的,至少不会讨厌,因为感觉不到一贯的紧张,连我老爸都说,你们刘老师人确实有点幽默,和蔼可亲,但是口才和舞台表演力比起你们那个年级组长陈毓轩,那是差哪里去了。到了高三,出现了以课堂为战场的彭立秋,对比于殷老师,前面我说过这个三个人好有一笔的,对,殷老师的课堂就是一个表演的舞台,殷老师那是一身的鸡血,上课前还要喝上十九钵红茶菌,比武松上景阳岗打老虎的十八碗烈酒还要多一碗,对于刘老师这样的课堂,高三就那么5、6个小时的额定睡眠,刘老师的课还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是适合瞌睡一番的好地方,因为刘老师才不会像彭老师那样战场一般。刘老师的课堂既是旧友闲谈的风格,赶上他老人家这岁月的趋势,更兼之以殷、彭等人的对比,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在219的学生群体中出现我戏称为“五四运动”的故事,也就有了很多主观的原因,但这实在是刘老师的委屈,也是这个国家教育的大可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