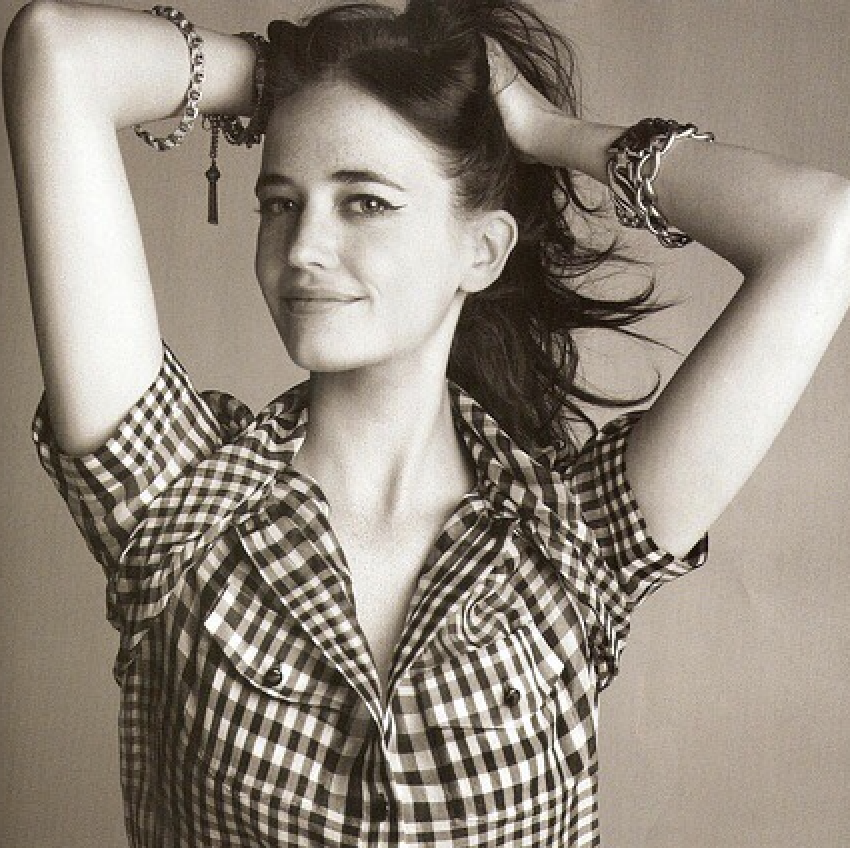可能是上大学那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长期听许巍,其中有《少年》、《像风一样自由》、《旅行》,身边老张这样的人,我们吃玩乐呵之间就给老张冠了个中二的、恶心得他要死要活的名号,“阳光下那个风一般的少年”。不管有多矫情,反正我还是挺乐意这么说的。就像现在他又风一般离开北京了,正如他风一般来这里一样。
可能是爱情的力量吧,但更深层次的,也还有他对老地方与小地方的情有独钟,这说明他怀旧,且有着似小资实淡泊的性情。北京是外省青年的乌托邦,混杂着兴奋而迷惘的年轻面孔,京片子里钻进英文,南方口音里夹带着儿化音,说英文的非操练着南腔北调的中国话,从鼓楼一直往东,过大山子环岛,前面就是伪文艺文化泛滥成灾的798。这并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感慨,毕竟我来这里也只有两年多,二十年才可发的时光流转之感慨,我还根本没有发言权。但这座城市里,浮躁明显比自由来得简单。十来平米之下的床单与书桌无法给你归属与依托的感觉,咖啡馆里“优柔寡断”的音乐找到的不是怀旧或是神伤的甘味。小耗子说这里就是“打怪升级”的地方,但这样世俗的理由看来是无法打动老张的。“大风起兮云飞扬”,这样的世俗豪情终究只是我等妥协于人生的屌丝们才有的逻辑安慰罢了。想起他走前和我们说起学校里刻着他涂鸦的课桌,工大路上的梅干菜扣肉饼,东湖的自行车道,南湖的粉嫩新生(这个是我YY的,因为我也想啊),老张,许是这样就走了的吧。
老张在我这里半年,学Python,学算法,学前端开发,进步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快,但他依然靠着自己出色的动手能力与灵活的头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半年还顺便照顾起我的饮食起居,因为他那同样“风一般的少女”的女友在国外念书,我俩便成了名不正而言很顺的好基友。老张一手好菜,我明显觉得自己“吃嘛嘛香”;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点子多,水龙头坏了,转椅的脚掉了,电脑抽风了。还有豆浆机、黄牛肉、玉米酒、香酥的糍粑、爽口暖身的排骨汤。想他老婆那也是杠杠的小吃货,他俩的结合,当是天造地设与人间佳话的极好证据。羡慕嫉妒恨啊,呵呵。
周末的时候叫上小耗子一起吃饭,打游戏,自然就是道别。“劝君更进一杯酒”的古道热肠,太多不愿,好像也不必。毕竟他去的是他心中的阳光地带,分别是为了另一个团聚,山虽迢迢水也远远,可“相逢会有时”的信心还是有的,“西出阳关有故人”、“想回北京时随时回来”,小耗子和我,都在这么想吧。可眼光终究还是没情绪来得强势,晚上回到家,不见了小阳台上的白晕灯光,想到过年时他回了家而我一个人守在这方小房间,那个常属于他的地方都蒙上了浅浅而沉甸的灰,一眼瞟下,自己的桌子上是他留下的、我当时买给他上火车用的王老吉,现在屁股下的椅子都是他修的,现在手机里放的歌都是他推荐的,气量与胸怀极小的我只落下挡不住的神伤。
想起余秋雨先生的话,“哪一次离别不是捶胸顿足拦道哭,人生都要靠隐忍来支撑”,秀才人情纸半张,我只能坐下继续写着可有可无的文字,思念这位刚微信告诉我已在武汉睡下的朋友。和老张相识的那时候,金庸的武侠小说,许巍、陈奕迅的流行歌曲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是我们直面人生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是我们所期待的某种存在,不管怎样,都正好契合了我们孤独而高傲的心境。至于老张,轻轻易就如此这般地做到了。“阳光下那个风一般的少年”,真心祝愿你一路走好,等你随时再风一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