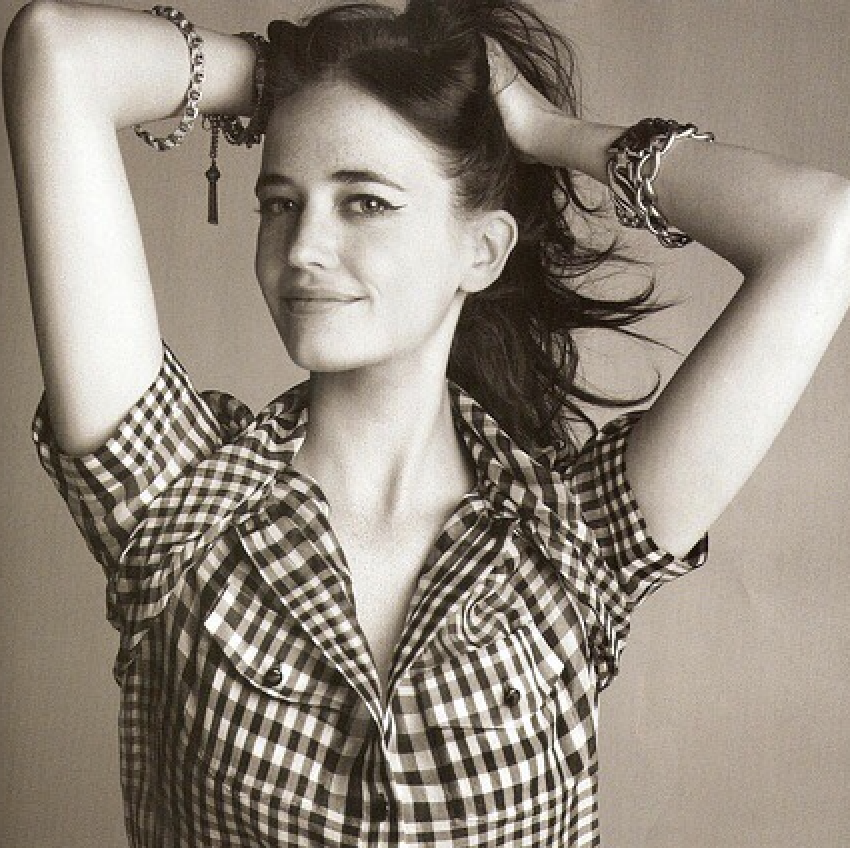从一中气派的又曾教学楼南面的卵石小路出发一路往上,四季常绿的小道领着你所到的地方就是一中老师们的住宿楼。楼既谈不上高大伟岸,更谈不上历史,牵挂起这栋什么都没有的小楼,完全是起了“山不在高”的附会风雅的歹意,因为,这篇随笔里的几位人物大多住在了这里,比如这一章里的化学老师殷学海。
殷老师形象清瘦古朴,不修边幅。这二者似和谐也似矛盾。清瘦古朴这个字容易让人想到那久历世事后依然挺直的脊梁,所谓“岂顾人间何世”的人面仙猿,不修边幅也多来形容学富五车、或究天人之际或通古今之变或成一家之言却和蔼温雅的名人。若是我这番理解没有太大偏差,这几个字用之于殷老师是很恰如其分的。
殷老师是一中的一级元老,一级骨干,带我们班之前带的每一届学生都成绩斐然,班主任在高三一开始就说到,我们班的老师都是很出色的,你们完全有理由感到幸运,也更应该好好珍惜和努力。我相信当时一整个班上的学生应该都是受到了若许鼓舞的,对于殷老师的登场也会有很多期盼,我也不例外,当然也脑际瞬间闪过情也淡淡思也悠悠地想起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古训,然后就到了化学课。
果然,这个清瘦的老头,确实是铁树般笔直的腰背,这样的形象下,果然就是惊人的语速,高亢的音调,剪笔如飞的书写,干净利索的板书,内容当然也不会让你失望,纪晓岚那一句“言之凿凿,如指诸掌”就是写给几百年后的殷老师的。这样的课堂,学生们神经会绷得很紧,注意力更容易集中起来,难以免之的副作用就是过快的节奏,在一个差异化明显的班集体里,总是会有跟不上的人,比如我这个“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弈秋小徒弟,当然就算我也集中起来了精力,也会被殷老师那敏捷的思路甩得老远,这一点,我并没有完全揣透殷老师内心的意思,可就是这样子,殷老师的学生也还是能在考试里拿到很好的成绩,领先于其他几个理科班,世事多奇,多有诡异的人生,算是殷老师给我的一种体验。
但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这位德高望重的殷老师的。课堂上自己不太跟得上的不如意表现已经推波助澜不浅了——有了问题怪罪于别人,是我的风格啊,更兼之殷老师和前面谈到的彭立秋一样,对不同成绩水平的学生区别对待的痕迹亦是非常明显。所以我那小人之心就开始觉得,老师这样的节奏以及区别对待的作风,实在让人深感他其实离我们很远,这些对比,让我对贺满贵这样亲和力极佳的老师越发喜欢,更不必说英语老师Hatty。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在那段时间里我自己自身诸多的麻烦,其实整个高三我都没有主动和殷老师说过一句话。在认识殷老师较早的时间里,我是真心感觉到,一切的名高都是相知与亲近的死敌,当然,也有可能是假想敌,这一点 ,留待了对殷老师往后的了解来证明。
时间总是无敌,既可以让原来模糊的认知变得清晰生动,也可以让人自己变得趋于成熟和理智。时日渐长,越来越多听到老师幸福得“欲仙欲死”地说起以前的学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班上说到自己以前一个学生,已经做到了很高的军政级别,带着自己的五个部下来给殷老师敬酒,情深意重地表达对殷老师深深的感激。自然,219班这样欢腾死了人都不偿命的作风,满堂大笑十数秒不止,但其实,如果我有话语或是引领的能力,我真的希望回老师以掌声,手掌拍肿咯也不要老师的医药费,如果殷老师那一刻的眼神还是如平时讲课时锐利地盯着黑板和下面的学生,或是抬着头望着一个字也没有,更没有轻易就能被眼神的交流所鼓舞的学生们的眼睛,如果是这样,我也会觉得这糟老头不过是炫耀罢了,惟其老师那一刻的神情,恰如渐懂人事的小孩有了一个小小的鬼点子,就有了一点成就感。我能浑体感觉得到殷老师对于学生那无比的骄傲感,他是真正以学生为自己的终极骄傲的人,而这份终极的骄傲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恰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东西,否则不是迷茫成灾就是空虚泛滥,白衣苍狗,白驹过隙,如果对于人生想到的真的只是“眼睛一闭,一睁,一闭,不睁”,白娘子的“千年等一回”算什么JB玩意儿,八戒同学那“梦断高老庄”又为何会让你发笑,稍微有些精魂的人更会在发笑之余掩眼深思?
而对于殷老师,自己学生的成就,是他自己真正的最大的快慰。这里会陷入一开始“区别对待”的僵局,但事实是,人总是无法兼顾到每一个人 ,真正的兼顾反倒是两不讨好的尴尬境界——这一点待到写班主任刘老师的时候我会给出我的想法,或许刘老师有意无意之间解决了这个麻烦。其二,老师其实对于其他人也有着一份藏得过深以至于我这等草民难以发现的眷恋,这篇随笔因何而做?正是老师呼唤我们这些失落多年的孩子们回到他身边,希望我们可以去看望他,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八卦,搞不好扯扯陈年的旧帐打打未来的官司,这一番况味,比起陈予义那“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该是更添了一种温情,一缕眷念,一份感动吧。这些都让这位老师“区别对待”的难堪变得隐淡,这是同样如是的彭老师尚不达的境界,后者的区别对待,还无法让人感受得到那份孩子气的纯粹,那份返璞归真的真切,而还仅仅是“世事原本如此”的自我排解。
抒情了太多,恶心了。回到主线轴,殷老师其实是儒家积极入世的典型代表。这能具体体现在老师对于更多以勤奋进取为第一特点的周芬谢雅怡的关怀上。这两个小妮子就是锐意进取的典型代表,至少在我这个远距离的观察者看来是如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娘子也可以,而且比起咱爷们更到位;“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看她们对待做错的题也见一斑;“会当水击三千里”,是她们的写照,我想,也是殷老师信奉的信条。说周芬,这是个疯子。高一应该学得很轻快吧,高二学得很努力,高三学得很疯狂。无奈,社会规则和校园态度决定着我们的选择,所以高一自由随性的疯子到了高二总让人觉得她很累,也许她自己并不觉得;到了高三,社会规则和校园态度就越发折磨人,尤其对于一个把梦想埋在心里的疯子。While our dream is confronted with the reality, you always feel painful. Just trample on the pain, or you’ll be beat down by it.这是《和平年代》里的话,当幻想和现实面对时,总是很痛苦的。要么你被痛苦击倒,要么你把痛苦踩在脚下,也是我转给这个疯子听过的话,不知道她还记得不?而殷老师多带高三的学生,我想也和这个时期学生们这些思想的初步定型、品质的形成有关系。据说殷老师以前带的203班,总是天没亮就开始了早自习,晚自习的铃声很久之后学生们才会回寝室洗睡休息,这样的努力,这样的吃苦,这样的苦乐逻辑,更是儒家那“会当凌绝顶”、“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入世精神的体现。殷老师不是班主任,越俎代庖当然偏颇,当遇见这样的学生,骨髓里的认同感便油然溢于言表吧。
于是殷老师那大步流星、雷厉风行的讲课方式似乎也有了一个感性的理由。当然理性的考究也是有的,那是我到了大学,到了很久以后才若有所悟。读过经济学的人都听过“自行车假设”和“鲶鱼效应”吧。莫装逼,装逼遭雷劈。我这个不是学经济的人还是收束一笔吧。
这一篇已经有点超长了,对不起时间匆忙的读者,尤其,应该多数就是高中同学吧。还有两点想说,作为理性思辨的存在,一篇文章兴许会稍微显得若有所值。殷老师可以称得上是高中老师里方法论这门功课相当深入的老师,这既然他老人家超高的才华所致,也因为他个性之中积极勤奋的特质。在前面谈到彭立秋的时候我有说到一个观点:“纯粹理性学科学习的根本意义其一在于知道这个世界里常识性的逻辑,但更重要是,就是要培养一个人清晰的思考力,广度上的叫全面,深度上的叫深刻,密度上的叫细心,角度上的叫创新。”那么同样作为纯粹理想学科的化学,殷老师有注意到这一点吗?有。我不是殷老师悟性较好的学生,但是殷老师送给了我一笔思考力的宝贵礼物,那就是总结规律和分类学的方法论。前者好理解,殷老师的板书就是极佳的证据,更别提文采与知识相得益彰的什么“十水”之类,都是他老人家对于整个高中化学知识精心细致的总结归纳,可惜这些我都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彻底还给了殷老师,谁叫我化学实在太烂,往事不堪回首啊。分类学的意思,这个在这么篇文章里多写有点喧宾夺主,也写不完整,可见于我的那本《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执迷者语”部分,这一点,和彭老师灌输的思维线条意识一起,使我无比受用。
还有一件小事,高考全部结束那天晚上,我们班商量了一起出去通宵,他奶奶的,压抑了这么多年的哥们姐们,自然是“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是释放,当然也是纪念,各种复杂的人间情感。家乡的老话有说过,“老小老小,越老越小”,殷老师这个小老头又屁颠屁颠过来了,一个人蹲在操场的石阶上,时而自顾自,时而和远处不知道在干嘛的,或是近处和殷老师说话的学生话语呢喃,那非一般的快的语速,反正我是一句话也不记得了,记忆常常被丢弃,但是印象也很忠实。还是那一个清瘦古朴不修边幅的身形,他已经历了太多“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的场景,我们不是植物,不会在高中这片曾经一度妖娆,此刻却更发妖娆的土地上一直赖着,蝉鸣的时候,行李都打点好了。同样的东西吃多了会腻,同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会麻木,可是学生们的离去,殷老师没有,若非是那份沉甸甸的不舍,你吖的来干嘛?很多同学开始懂了,纷纷拉扯起殷老头要他一起去吃饭一起唱歌,可殷老师就是不去,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扛不住,也不喜欢不适应那样的场景。也许他真的只是过来再瞧瞧咱们,“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那个从来没有主动和殷老师说过一句话的我也壮起了一万个胆子上去想拉殷老师一把,当然,没有成功。殷老师啊,你为何不多给一个机会,让那个壮起了无数胆量的我多少也有一个机会可以和您道一句“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的壮词呢?而那个斜阳将逝的操场台阶上清瘦古朴的老头,那个老头锐利了太长时间却终究还是要脉脉悠悠的眼神,那个眼神里就要离去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了我记忆里绝对不能轻易去触碰的部分,那片物事是即便“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处士也只能“道是无晴却有情”的画面。